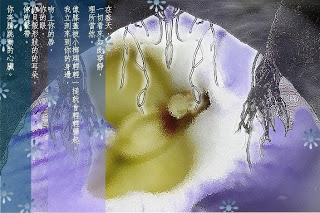*****************************
「原來吵完架打砲那麼爽!」
「是嗎?那要我再幹給妳嗎?」
「我要,我要。再幹大力一點。把我弄壞。」
「還是以後我們都吵完再幹?」
「那你得有本事讓我吵完後還想被你幹。」
※
這一天,我和她剛吵完架,做愛時出現了以上的對話。
其實我們不常吵架。而她的氣通常來得快、去也快,頂多是睡一覺
起來就算了。不管我們吵的原因是什麼,我知道她維持生氣等待的
是什麼:就是等我哄她,偶爾也讓她當當公主。
我的脾氣也硬,不是每次都會低頭。有時候抓準了知道她氣不久也
就放她去;但有時候想到她平時對我的好,就會扮回孩子氣的嘴臉
逗她。
我記得國中有一陣子會寫日記,隔一陣子,老師會抽空收去看。有
次我記下了和同學起衝突吵架的過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經
驗:事實上,誰對或錯早就已經不重要了,只是誰也不願意先開口
和對方說話。我印象很深,我思考了幾天該怎麼做,卻沒有得到答
案。有一天假日,他來我家找我對我說:「那天的事,對不起,是
我怎樣……」在當下,我完全不記得他做錯的事,卻被自己羞赧的
心境所教訓,趕忙著說我也有不對……
記得老師在那篇日記上寫著:「要讓別人認錯的方法,是你先為做
錯的事道歉;要讓別人低頭的方法,是先低下你的頭。」
對待身旁的朋友如此,對待一個與你共枕相眠的人呢?
「主動」是一種智慧,但往往很難跳脫「對」與「錯」的執著之中。
靠,寫到這邊應該是文不對題,零分,所以回到主題。
所以這天,在她心裡已經原諒我但表面仍等待著被哄時,我側身便
插了進去。
「走開啦。我有說要讓你幹嗎?」
「你不用說我知道妳有。」
「你屁啦,我還沒原諒妳也。」
「你不用說我知道你有。」
「你以為你在演《與龍共舞》嗎?」她的聲音開始嬌喘起來……
很妙的感覺:像兩個裸身的人,隔著一面冰牆。破冰而後擁住對方
感受到的體溫,格外溫暖,情慾也變得火燙。
我突然推開她,爬至床頭幹進了她的嘴,她的眼神、表情讓我失心
的硬挺不已。
「親愛的,好吃嗎?」
「唔……」她扶著我的屁股自顧自地往嘴裡塞。
—
@pe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