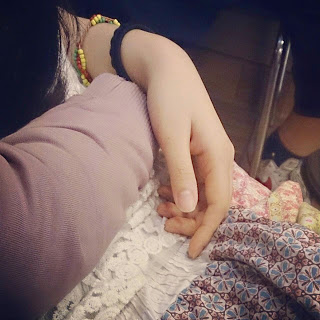Sink結束後,我渡過的是十分不安的三年。那是十分隱密的不安,難以說明,曖昧、混亂而引人恐懼。我甚至不曾試著誠實的對自己說過這些事。自己不熟悉的文體,顯然成了極好的出路。我開始依賴許多陌生的事物,舊日子許多熟悉的東西,不知不覺就擱在一旁。
替代。A說,「你最大的問題就是自我中心」。現在想來那是極為取巧的說法。他所說的「自我中心」指的並不是自私,而是在心理的意義上的自我中心,亦即認知的根源性。有一陣子,流浪的比喻總是不自禁的在心頭,在過馬路的一瞬間,在發現自己失去了某個據點的時候湧現。那是一個虛假的想像,但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撕毀虛假的姿勢,總是軟弱無力,我知道那是一個虛假的想像,但僅僅是「知道」。事實上我哪兒也去不成。
一對相反的圖式在我心中爭戰不休。常常一曲還未唱畢,一時我覺得顛沛流離無定處,一時毫無變化的地方,又讓人覺得驚惶。樓房與另一座樓房互相吞噬,改建又改建但你說不出那股怪異的尬梗。你知道無論拆除了多少殘樓,新房中隱密的一處,始終有私下賄賂、交易出賣他人得來錢財的人。颶風撕毀每一扇窗戶,可是動搖不了人們的冷漠,他們在沙暴之中掃地、煮食、性交,稍有思想的人只用報紙,去遮掩房屋的破洞。「現在,有些人可以隨時搬離當地–任何當地,有些人卻只能束手無策的看著他們唯一的當地從腳下溜走…(Bauman, 22)」
厭煩,一切都令人厭煩,厭煩是革命之母,厭煩是一切的開始。沒有真正的改變,只有改建而沒有改革。一種特殊的,時光與地理徹底決裂,破碎的情感只是背景,只是開端。我在破碎之中穿行,心裡知道屬於我的地方已經完全破滅、消失,並且在心理強烈抗拒著一切有關於逝去的傷感。一股痛苦而強烈的意向引導著我,不斷的突破,不管會突破什麼,不管要突破什麼,絕不能停下來,然而要向哪裡去呢……暴力的想像吸引了我,擄獲了我,性的意識受到遠古、潛在的刺激,幾乎每個女人都產生了強烈的致幻性。
某一種處境—-我不確定是怎樣的–時常刺激了心中一股相反的欲望和幻想,我不知道這種處境是和什麼互相關聯的,它大體上是以空間的比喻為戰場開展的,越能打破自己就越能呼吸自己以外的空氣…然後窒息,風化或腐敗。宇宙。
當我喜歡上越來越多我所討厭的事物,究竟我變成了一個更多元的人,還是只是變成更讓以前的自己討厭的人,或是更善於妥協的人?「…這份『不成熟』是自己賦予自己的,因為『不成熟』的根源,並不是缺乏知識,而是缺乏決心,以及缺乏了在沒有他人引導的情況下運用自己的見解的勇氣……要敢於運用自己的見解!(Kant, 597)」
和「某一種處境」深深牽連的是「斷裂」。
我開始依賴許多陌生的事物,包括最理所當然的那些。笑容。
一開始寫的時候,幾乎什麼也寫不上來……空洞、乏善可陳。其實寫了還是空洞。嘈雜以一種終極瓦解的樣貌浮現。自己聽不見自己,他人也聽不見自己,自己也聽不見他人。我不容拒絕和打斷的告訴過我最好的朋友I,我將他的身心當作暫時安放我的自尊之處,他不置可否,我不可理喻的感到安寧。我說,但我不相信我說了什麼;他人相信,不是相信我,只是暫時相信了我的話。
最初的斷裂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Sink以前。當時我什麼也沒有警覺。
斷裂之間的一切也是斷裂,斷裂與另一種斷裂之間,沒有共同的原則。
也許很多很多幻覺是唯一共通之處,絕大多數時間,我認為一切的感覺都是幻覺,無論是腳踏實地或不切實際,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覺。痛苦或安和也是。最可怕的是,我以為連清醒也是幻覺。
日益生長的自信、抽象風景、急遽的迫切性、猛烈萎縮緊閉、朝著彆扭的方向錯亂的努力、厭棄、嫉妒、強烈的自豪感、邊界模糊、等待、搖擺、背叛、被剝下的鞘翅、旋緊的突齒、荒謬、改造工程……自由的終結。
斷裂的開始是一個樹立自我核心的嚐試:一個自行旋轉的嚐試。
K問我還聽不聽日本搖滾,他說他的身邊,找不到一個人願意和他一起喜歡《瞳之住人》,甚至就連他的男友。我沒跟他說,我這幾年是怎麼喜歡上口琴的。
寫e-mail給很多年沒有來信的B,隔了三個月後,B居然回信了。他問我一個和偏問的一樣的問題。他問我過得好嗎,以及還有沒有在寫作。在他的記憶裡,我仍是一個寫作的人。
和A的對話逐漸乏善可陳,我們很少再思辯了,最思辯的是我們各人的小情小愛。他說我是唯一懂他的人,所以他不理解我為何離開。我不再和他聊到天亮
了。
某一天結束之後,我經過了遊樂場。在遊樂場或網咖所拍攝的幾個鏡頭,是《共犯》中最讓我感動的鏡頭。青年一個人獨自面對龐大的錯誤聯想,他不善於言詞,至少不善於揍人和逃開以外的解釋。當他孤獨的時候他在網咖(誰說科技缺乏人性?),螢幕射出斑斕、呆滯而孤寂的光芒。我投下了一道太鼓,死在了第一首歌。Night of Nights。原來現在的遊戲這麼難。
和I開了一個讀書會,討論卡爾波普或葛蘭西。有些時候我們也討論隔壁的女高中生的大腿和髮型,還有女OL的胸部。回家將一些火車上冒出來的,零碎的想法寫在網路上,也有人喜歡。有時候也會想,可能我不是一個像我所認識的那麼需要日本搖滾、寫東西、思辯或打遊戲的人,可能我不是一個像自己所認識的那麼愛L的一個人。「我們之間所擁有的並不是愛,而是某種極其珍貴的,近似於愛的原石那樣的東西」,我一個草稿裡寫的。I有一次說的話類似我需要懂得如何讓自己的想法成為現實,他說我有旺盛的思辯能力(這大概是我唯一優點的意思)。
許多「關聯性」從我身上脫落的時候,許多現實動搖起來了,我常常不確定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就像那句歌詞裡面寫的),在家時我常常愛撫我的西裝,我買了好多件我也許穿不上的西裝,就是說不上來的喜歡,心裡模糊的襯著一個上身了會很好看的印象,布料觸手就感到安寧。不再從事任何一樣原本好好的東西,打破了那些以後,我的人依然沒有戲劇性的轉變–理所當然的。只是我失去了指認自己的象限。我無法再說,我依然是個喜歡日本搖滾、喜歡寫東西的人。
我並不討厭起寫作或日本搖滾,但我無法形容那種,你和你本應理所當然熟悉並熱愛的事物產生距離的陌生。我愛上了一個個稀奇古怪的玩意,吃下了一種種我原本討厭的食物並且感到驚異,拋棄了一樣樣我深愛的東西,沒幾秒又後悔將他們撿起,一切只憑感覺。我最近愛筆。
在什麼都沒有改變的條件下,什麼的意義都改變了。追逐暴風,最後追逐得太盡。我做著那些我以為我會痛恨的事物,和我以為我做著我以為我會熱愛的事物一樣無感。吃著美味的食物,帶著暈眩的惡感卻油然而生。不,我並不痛恨自己的身體或碟皿中不知名的動物殘骸,但我是否「屬於」那些事?也許我喜愛那些人或事,只因為他們折磨我的日子尚少,而我以為這樣的日子就是「關聯性」。
「不能引誘他人為你受苦的,便不是真正的才能」,某一次在另一篇草稿裡,隨手寫下。許多時候廝混的人們,哪有豪豬的壯志,哪有堪足以豎起防衛的力氣和怒意,只是像蛇或蚯蚓一般,朝著陰濕地裡一窩同類最沒抵抗力的被捲進去。「毒品、宗教、藝術和性(甚至是幻影,都只是為了避免與自己面對面而存在的(Murakami, 305)。」
有時候,那股陌生的、莫名其妙的排斥感是如此強烈,我甚至感受到那股源自胃臟的醜惡敵意,感受到那股敵意--自由的魔力,是如此的無與倫比。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我變成任何一種樣子,即使是機械般無能的模樣亦然,即使是滑稽的模樣亦然、即使是令自己不解、污穢或鄙夷的模樣亦然。一個國光幫式的俚俗人,一個古龍式的嘔吐,一個穿著西裝的馬頭青年。
我不愛這個世界了嗎?我在不知不覺間墮落了嗎?然而在我能回答「愛或不愛」之前,某種更基本的東西卻沒有被回答。「我愛這個世界嗎? 」或「我愛他人嗎?」這些都是絕妙的問題,但我連這問題的第一個字都無法回答,遑論世界或愛。愛是另一個跟斷裂一樣的問題。
最近,偶爾和I一起去拍攝廢墟。在拍攝廢墟的時候觀察I,畢竟他是廢墟中唯一的人類,這是拍攝廢墟的寂寞與危險之處。廢棄的眷村、醫院、被扔在一列破落海產店對岸的廢棄碼頭、突兀地插在豪華地段的集中式住宅…許多廢墟是政治與荒野的邊界。我想我能明白為什麼I會喜愛廢墟,對我來說拍攝廢墟和拍攝街頭的人群既相似又相違,那裡頭具有一種說不出的文靜與精神潔癖的氣味,在街頭你總是在從洪流中找出眾人那物體般無感性的一瞬,而在廢墟你總是在處理安靜的,身上卻彷彿有時光蠢動的死物。那些垃圾像是永遠不會傷害你一般擺放在那兒…引誘你靠近,那也許是現實生活中與網路生活最接近的體驗。花與螢幕、窗戶與文字,這是最吸引我的主題。那是一個「社會的相反」的圖像,在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裡,愛何其孤獨,孤獨何其可貴。
在社會裡,「如何成為更好的人」有時候只能被理解為,就像雞隻學習如何成為更好的肉,你總是必須抵抗自己性格之中溫馴的一面。「取而代之的,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不同的認識觀點的歷史,在我們的文化中如何人類如何『變成』主體的一種歷史」(Foucault, 777)。「只能被理解為」…只能是如此嗎?我不想說自己受了「傷害」…傷害、孤獨,這些事的確存在,但那並不重要。最初是傷害,但越過了警告、傷害、暴力以後……那背後存在著某種真實的,絕對性、壓倒性的情緒。
斷裂,不是在人際關係上與人們決裂。血緣是個謊言,長久而溫柔的關係也是,羈絆和諾言也是。如果不用那些來遮掩,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之間根本的異質性,許多人就無法生活了。他們不能理解愛侶為何要「忽然」狂熱的吸吮他人的雙唇,不能理解兒女為何要「忽然」渴望被陌生人捆綁起來抽打,不能理解父母為何要「忽然」狂怒起來,違背每一個自己所慷慨訴說過的理想……不能承受斷裂的人渴望這世界上有某種簡單的關係,有某種可以理解的生活。他們甚至願意成立一個官僚政府來保證這樣的生活,如果他們可以的話。2014年3月是一個震撼日子,9月也是。
A曾說,對他而言唯一真正的政治只有恐怖主義。他所說的當然不是激進軍事行動,但作為一個比喻,你不得不承認那股黑色幽默之中的顫慄真實性。許多人將斷裂理解為斷絕關係,理解為一種為了逃避幻滅而啟動的自我保護的意志,但即使是認識到了徹底的相異,關係還是斷絕不了的,所等待的只是溫柔罷了……在那個龐大的屠解場景。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不斷聽著《寶貝》。從前從不覺得這首歌好聽,但我喜歡那句「讓你喜歡這個明天/讓你喜歡這個世界」。也很想將歌詞朗讀給我的寶貝聽聽。我覺得這首歌可以令我更有力氣一些……謝謝我的好朋友偏執狂,應她的提議,寫這篇文章令我想通了許多事,我覺得我好多了,這對我來說很重要。謝謝你,Miss Arrog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