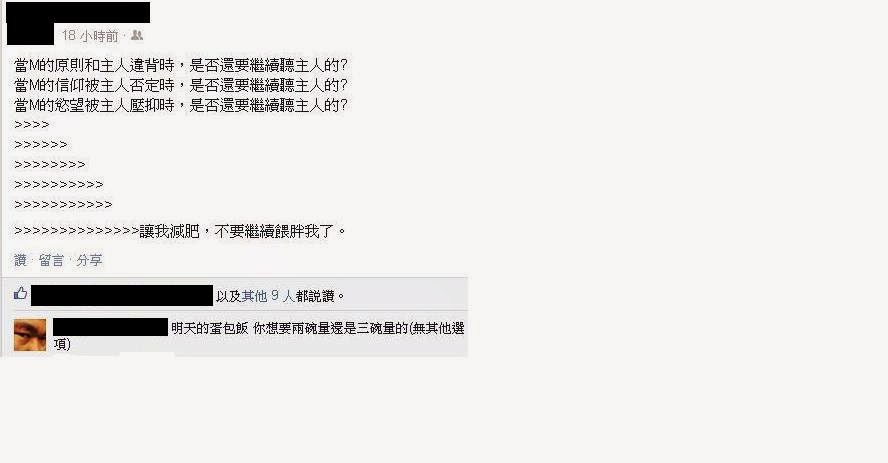這是一段已經落根的自己,用過往的自己,留給未來的自己的文字。
分類: 未分類
那一年,我的欺瞞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冬夜的西門町,儘管在網路上我們早已知道等一下就會探索彼此,我們還是先坐在一起吃著義大利麵一邊看著來往的路人,談著之前在學校的事,社團,家庭和對人生。
吃完早餐,一起進了她說某家之前習慣去的旅館於,勾著她的手一起上了電梯。
進房後,她脫下外套,就一把被我從身後抱往。
有點豐滿形的身材,第一次抱住她感覺全身都軟軟的,很舒服。用舌尖挑弄她的耳朵的輪廓,舌尖冷不防的舔伸到耳廓中間的部份。呻吟聲開始在房內傳開來,我慢
慢的摸著她全身,再讓她轉過身來,一推就讓她倒在床上。
對於她的柔軟身體,總覺得應該好好疼愛她,做愛的過程大概是那幾年我最溫柔的幾次之一。
完事後,我們一起在西門町逛街,她接起男友打來的電話,用冷漠的聲音說話。後來的第二次,第三次約,讓原本以為是一夜情的情況有了改變。
一個月後她和男友分了手。現在想起來,應該讓這關係停在肉體上或乾脆終止。
後來,是我向她告白的。
這段交往兩年的感情,讓我們愈來愈痛若。起因還是因為,我們終究不是像正常的情侶一樣,而是基於肉體、寂寞、想要陪伴,而在對方身上索求自己缺少的什。
某次做完愛,我們談到結婚,那些我們談了很久但最終沒有解決或面對的問題。她告訴我,我從來沒有真正的說,愛她。
我們明明知道在這段感情中只想在彼此身上找尋那根本不存在的凍西
。她對我的種種要求和限制,希望能得到安全感;我從肉體歡愛和約會中解除寂寞,天真的以為這就是喜歡和愛。
破裂其實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爭吵愈來愈多,最後在怒氣中大叫,我們分手吧。但即使如此我們也沒有乾脆的分開。我喝醉了,用著醉意到她家去見她。坐在她家附近的公車站的位上,我們知道彼此的關係無法再修複,但她仍用輕美的聲音安慰我。
我知道我們彼此不能再這樣傷害下去了。 分開後,我用半年時間整理了自己,真正的讓這段感情過去。
最近,覺自己慢慢失去和人相處的能力。同時,偶而會看著她的FB,或看著她的網路相本,猜測她的近況。也想起那一年,人生中的一課。
RE: 那一年的欺瞞
有一晚偏惆悵的對我說,不要隨便和一個不幸的女人談結婚、未來一類的字眼,她什麼都會當真。我忘了那晚我是怎麼回應的了,只是想起了,那一陣心頭無從打發的悶礙。
那真是寂寞至亂的幾年啊,L離開了,我仍失態而無以自處,除了夜夜緊捉著一把聲音沒有任何可以安放之處,但90%的時間裡,我不會得到那一把聲音,那個時代,只是iPhone剛剛流行的那幾年。在90%的時間裡,能賴以驅散死寂的只有反覆播放《霧港水手》、《重慶森林》,聽累了就玩PERSONA 3。H便是在那一晚晚裡與我相濡以沫的一個迷失的靈魂。
90%的時候H對我說大大小小的謊,而我只對H說了一個。
追求H這件事多少換來了好友R的鄙夷,鄙夷我口口聲聲忘不了的愛容易的便對一點點的性衝動潰敗。我是一個濫情的人,容易過度意識到另一個人屬於性別的吸引力,在我們這個世界誰不如此呢。那個時候H有一個得不到的情人、偏有一個得不到的情人,我和A寫著永遠無法寄給永遠的信……無論雅俗到頭來都是同一件事。
H有一個混濁的靈魂,現在想來,那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吸引我只是因為那個混濁的靈魂象徵我貧乏的經驗所能定義的一切墮落。他是我一切喜歡的相反,但那時候我深信我的未來不可能會更糟了(我大錯特錯),我想要愛,我想要將那無依的熱情全部埋葬,而我以為我會有一個墓園,至少是可笑而平凡的,到頭來我還是審判了他。H幹了一個又一個玩伴,玩伴這個詞就是他教我的,他說除了愛,他什麼也幹不了,什麼工作也給辭退,然後他就像一部壞掉的收音機唱著同樣的歌那樣說著同樣的事。把他修好,這件事讓人滿漲著奇異的欲望,幾乎和某些男人迷戀於把他弄壞一樣。但我失敗了,一部分的原因是H是個怪咖,而另一部份則是因為我是個混球。
依稀是H去和哪個人痛快幹過的某一晚,我不知道趁著什麼便對他說,假如等我離開現在這個地方了,而那時我倆都仍單身的話便結婚吧,一類的話,也許說得精彩吧。H不置可否,大約覺得我只是喝醉了,然而當他開始對我變得溫柔的時候,我知道某些東西悄悄改變了。
然而在另一個可悲的世界,什麼也沒改變,H照樣幹他的男伴,我照樣聽著墨鏡王的電影,我們倆照樣感到無趣。有時候我毫不掩飾對H的嫉妒和對他的欲望,以至他也覺得困擾的程度,畢竟我根本不是他在意的那類型啊。
後來是怎麼散了的我也不記得了。離開那個地方的時候,我並沒有和H說,到了台灣之後,我便追求了其他女人。MSN也收掉了,除了寫過給H的一些零散、怪異、莫名其妙而充滿性的隱喻的故事以外,死無對證。後來H在臉書上找了我,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問我要不要一起玩UL,他可以教我怎麼玩,而他以前是從不會這樣對待我的,也是那個時候想,我可能對他犯了錯。
後來的那一晚,偏幽幽的說起她的失落,從偏的口中說出來卻命運暗合,像是H的人生寫照一般,喚醒我對H的回憶。在那不堪說出口的迷亂青春之中,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軟弱的,受到蠱惑的人。然而我卻不知道一個無意的諾言反而玩笑般切進了一個放浪女子的宿命……那一刻我相信我的謊言已經會是他眾多傷害的一頁,已經不可能談什麼原諒或和解,我開始相信某些致死的誘惑比如婚姻,比如讓我們變得更好,有時候是很卑劣的存在著的。
Re:那一年的欺瞞
RE:性冷感
得逞 & 無情
I
一大早RAY進了我家,出現在我的房間前。
原本說好要出門去一起找咖啡館窩著,看書。
前一晚熬夜的我實在是累得起不來,捲著被子。
來嘛,我們一起當共犯。
「什麼共犯?」
「賴床的共犯。」
這樣溫溫的在被窩裡待了半小時,她還是不死心的想叫醒我。 離我們原本要出門的時間已遲了快兩小時。我終於從被窩裡脫身,換著她捲著被子和我說話。
「其實,昨天做完愛後,我有偷偷哭。」
「所以我才有問妳,為什麼哭啊?」
「我總覺得我喜歡你更多,比起你喜歡我的程度。」
我笑笑沒說什麼。
「你知道今天為什麼我想來嗎?」
在被窩裡的她,眼睛閃閃發亮。
「因為我想見到你。而且只有在做的時候,你才是我的。」
大概是這句話,和她陷在被子裡的姿態。我開始吻她。下場又是一場歡愛,衣衫不整且而快速。在頂點後,她原本 苦惱的表情轉為平和、滿足而且帶著愉快的笑。
我說,「我覺得有一種不情願被說服,而且被你得逞的感覺。」
「但我剛剛說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
II
下午終於還是出門了。
從鋼筆店試完幾個入門的筆款,讓她選了一枝。
走出店,一起搭公車,送她回去,
我告訴她,我知道她的某些感覺,但我只想要隔著一種距離看著。
「為什麼?」
「如果是別人,或者大多數的人,她們知道問題,會給你建議,會替妳發現問題,會幫你整理心情,甚至在妳還不知道的時候,他們就會開始做這些事情。」
經過松山機場的時候,我想到昨天早上落進基隆河裡的那架航機。
「但是常會發現,人們都太急著要處理,處理自己的,和處理別人的。但到頭來,妳可能也沒辦法靠自己發現自己的情緒和問題,而別人最後也未必能處理,但會拉太多的責任到別人自己身上。這樣,別人想照顧妳,其實沒有照顧到; 妳以為他原本會照顧到妳,而對他產生怨懟。」
「你好無情。」
「我不是無情。我知道那些,只是我不能代替別人處理。」
然後,我又想起艾,幾年前在自己的新聞台上寫下和孩子的互動。
相對於我的年紀,RAY與其說是少女,有時更像孩子。
但終究,她不是我的孩子。
她得自己長大,跌跌撞撞,或許遍體鱗傷。
RE: 不淨
宮殿,多麼古老、華美、隱喻賦予能動的暗示,如果可以賦予自己的心象一個空間的比喻,我會說是超級百貨公司,海瑟迷失的地方。那是一個自戀的場所,因此鏡子只會被擺在最能讓人自卑的地方,和其他攬鏡自照的人共用,或是在封閉孤立的更衣室(充滿了監獄囚室或獸欄之類的流水線意象)裡。假如時裝是種自慰,時裝的狂歡者則可以分作兩種:公然猥褻的,和挾帶猥褻走進私密之處的。
想像一下百貨公司在核災後空無一人,頹唐卻仍然屹立的模樣,也許你會不情願的承認那是我們唯一真的用心建築的文明(而不是古蹟或性工作跡地遺址),海瑟在焦黑、牆壁出癌滲血的百貨公司裡孤寂的疾行,一兩隻皮膚潰爛的犬隻對她低嘯著,不時在走道轉角從背後追上再猛烈攻擊…
許多人曾說我是陰性的,當時我皆不以為意,但是現在想想,其實我從不是戀父的。
逐漸在詩意的層次上喪失了對L的性慾之時,在另一面,我也感受到暴力對自己的召喚正在逐漸變強,就像是一筆龐大的金額被一小筆一小筆的劃撥進陌生的銀行帳號一般……那是一種宗教,而人們迷信暴力萬能的程度並不下於對猥褻的迷戀。B近來迷上勾引我動用蠻力,使出力氣強押著她的時候,自己體內某個齷齪的部分也從B那邊神秘而奇異的覺醒、獲得滿足。那是一片大霧迷濛的海,我望進去但沒有看見任何臉孔。百貨公司的鏡子,現世的魔鏡裡,沒有任何一個照鏡的人有自己的臉孔,全部都是光滑的、官能的。對布希亞來說,那是色情的一種:光滑、純潔、封閉的、不可穿透也無力言說,因而在那恐怖感的背面正是一種逼近「不淨」的怪異感受。原始的恐懼。
海瑟倉皇奔走,海瑟追念著父親,四處都是行走的腐肉、銳利的鐵絲、巨大的蟲蛭和牠們滴墜的膿血與精液,她在找一個房間,一個有小風琴樂曲和打字機的房間。
「…因她是假如那個體化、分異化若要發生,便必須預先排除的『非身體』、猶如無形無相汙穢的流體…」——《SEP》
為什麼呢?為什麼後來再也沒有辦法理解她們了?A說,那些說自己靈魂像個大叔的女孩從來不必面對性無能的頹唐;那些自稱具有少女心的男孩也從不必以飢餓削細大腿。某一天接到她的電話,她失去了平日的譏誚、俊挺與自持,哭嘯著說她是不是做錯了這件事、這件事、和那件事是不是,為何所有她愛的人最後都不再理她了。
「我覺得他說得對,只是他為了讓你聽懂而用了比較直白的語言,你必須得意識到,吸引你的其實不是男人而是陽性這回事,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永遠不可能成為、也成為不了一個符號、一個象徵。」
在我喊出這段話的時候,我覺得海瑟彷彿也如此吶喊著。所有被遮掩在西裝、皮衣、割破牛仔褲、斜方肌,那些被遮掩在侵略的權杖之下的東西全都衝破了象徵之鎖,流出憤怒的白液。是的某種燦爛失色消潰了,但那並不是閹割。有時候振安、志勇他們會找我,我總是拒絕他們的呼喚,為了心安理得,為了安身立命而將我唯一經由互相毆打得到的友情隔絕在某個距離之外。L在九年前狠狠戳破了我為自己樹立的虛幻性,一種自我繁殖的陰/陽性,但是竟然是在那麼久以後,我才能認識到他的愛。假如象徵的陰性之於實在的陽性,只能在不淨之地持續放浪,那麼就給我一個吳爾芙的房間,給我一台喃喃自語的打字機,來看我的人會看見的,我按下打字機的「P」鍵,彷彿按下琴鍵的姿勢。
我會寫信給海瑟的,是時候該由她來撕掉那些信了。
Re: 在最好的時候遇見你
帶球走
不淨
以下是最近幾天的喃喃自語。
在和寂一起去尋找晚餐的路上,聊著最近一起讀書內容時,他提起克里斯蒂娃說過關於賤斥的內容。
人對於排泄物處於一種矛盾,在排泄物未能離開身體前,或許也不會意識到排泄物的存在,但排泄物離開身體後,為了種種原因用儀式規則讓排泄隱藏起來。
也想起佛教在教人放棄執著時會講的不淨觀,把人的身體分解化約為種種不淨之物,血膿水骨毛髮內臟穢物,人不可能對這些感到舒適,如果能經由觀想看透這些,也就可以放棄對肉體的執著。
想起剛好在一星期前,住在加拿大的娜娜,在LINE上幽幽的說:「我不太懂擺弄垃圾和用顏料畫圖,還有精神分裂患者用糞便塗牆差別在哪說,是媒材的細菌數量問題?」
這個月開始看書練習關於一種叫「記憶宮殿」的觀想,據說是透過想像和記憶有關的事物,詳細的運用幻想力建立起記憶的建築,長期的練習和擴展之後便可幾近無窮的記憶下任何事物。我沒有這麼大野心,開始練習的出發點只是為了想回顧一些生命中模糊的經驗和感受,並試著找出適當的位置去安放它。
也因此,十年前或二十年前一些未曾深刻再重新想過的事情,又被我拿出來放在屬於自己的展示台上,觀察,檢視,決定是要丟棄,還是放在那個我自己建構出來的「自己的房間」裡。
我發現其實,在性方面,我仍然記得過去和我相處過的女人們,但卻不是經由直接的記憶記得。例如我記得的SU是因為我還能想起在宿舍後方洗衣間內,在昏暗的日光燈中撩起她丹寧布長裙,指尖和掌摸上她被絲襪裹著的大腿;記得MEI是因為想起在淡水的那夜,歡愛後放空的看著落地窗陽台外,遠方海上的光點,不知道是漁船還是更為神祕的燈火;記得小平則是她異常冰冷的舌尖;記得KEY則是因為在我大學當年的租屋處,她在我的上面擺動腰力時,我還記得當時日光燈那蒼白的冷光……。
只要能想起這一點片段,那麼隨之而來的形象就一點一滴的,如同一群牽著手圍著營火跳著舞的人,那些原本模糊的臉、穿著衣服的花色、頭髮的長度或表情,慢慢清晰起來。只是其實也無法再確認,到底那些是真實的情況,還是自己事後再從少數材料,依照著自我暗示和滿足所建立起來的另一種記憶。
在揮灑和排列這些材料的同時,也不禁懷疑,一定有某些東西被我關進了記憶裡的地下室,是我不願意去想起的。就好像那些是自己排泄後不願再見到的。
曾有一段時間做著和蜘蛛和節肢動物有關的夢,另一段時間常做蛇類吞咬和緊纏自己的夢。不常做夢,但如果醒來還記得,那麼都不會是太愉快的。
記憶宮殿的練習目前才剛建好起居室,關於自己慾望,我還沒確定到底要安放在臥室,或是再創出一間遊戲室,甚至某些是否應該放在廚房,關於窒息和迷離破碎的,是不是就掃進地下室,並且創造出怪物來看守?
記憶不是純的,篩選是可疑的,回想充滿了不現實感,發現的不淨也是自己的。我很高興能接受不怎麼純淨,但確實活著,並在各種事物中品嚐到不愉快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