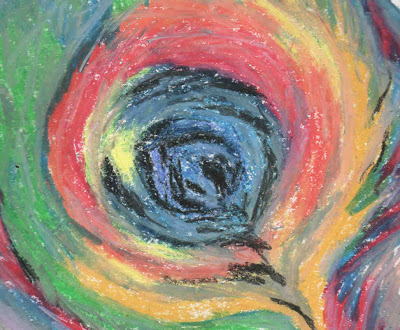文/Faith2010
男人撐著傘,穩穩走在雨中。
女人著漆皮黑色三吋高跟鞋,雨溼的木質地板讓細細的鞋跟打滑了下,合身的細黑條紋MaxMara套裝,抵擋不住突來的暴雨狂寒,手指、肩膀、嘴角簌簌發著抖。
大腿內側肌肉也輕輕顫抖著。
不是冷的緣故。
遞過空出的手,他的左手挽住她的右手,男性專有的厚實體溫逐漸穿透絨衣,穿透寒雨涼風,離女人的身體越來越近。
越來越暖。
她的手指依然受雨氣所凍,像承接了一整個冬天將下未下的雪。氣候變化混亂,搞不清楚,何時要著暖,何時要避雨,何時又該裸露美好的腿。身體倒是很穩當地,安定在他氣息所及的周圍。裹在合身黑色細條紋薄西裝外套裡的臂彎,傳來另一個人的溫度,顫抖的肌肉逐漸緩和,放鬆下來。
放鬆。在這個男人面前。掏出尼古丁含量0.6克的涼菸,點了起來。清邁機場新買的曼谷包,站在高架捷運前,遲疑很久,終於決定走進那家店舖選購,法式蝴蝶結,秋香綠,絲綢緞,菱紋格。
「最後兩根,抽完就戒了,最近抽太多了,一直抽,一直抽。我不喜歡這種上癮的感覺,該停了。」女人說。
「想抽就抽。」男人靜靜地說,「沒有關係。」夜裡影子拉得很長,像慢了下來,暈黃霧燈壟罩下,斜斜撒落的雨絲。「在我面前,妳想做什麼都可以。」
脫去她的薄西裝外套,解開腰腹間的雙排扣,拉下左袖,右袖,將外套自肩膀上剝離,完整露出底下亮絲白的蕾絲襯衫。略覆薄繭的大手,伸進襯衫裡解開金銅色內衣的背扣,緊緊熨貼著臀部的細黑條紋西裝長褲,底下紫紅色的緞質丁字。
「張愛玲一樣,把自己養成紅綠鸚鵡的一個女人。」他心裡想,沒有說出口。是胡蘭成這樣描述張愛玲。她不是張愛玲,他不是胡蘭成。他們不在動盪的戰亂時代。
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他們在這兒,此刻。
疊好脫下的衣服,整齊放在床頭,指甲修剪整齊的手指撕開鋁箔包裝,套上保險套,像安放著一件舉世美好的裝置藝術。只為她創作。
她赤裸著等待,深吸一口氣,右手撫上左胸挺起的乳頭,大腿內側肌肉緊緻著,微不可見的深層收縮。
扶著她的腰,摸著陰道口,一片濡濕。從背後插入,很慢,很慢,感受陰道裡每一處被陰莖推擠開來的皺摺。深深呼出一口氣,再深吸一口。彷彿此生,她正是為他而生,每一吋,每一分,完美熨合。
她看不見他如何進入。她想像,自己的身體怎樣在一片黑暗無光中被他撐開,又怎樣隨著他的抽出而閉合。每一吋,每一分,開了又合。
男人那雙溫暖、略帶薄繭,平時用來修整器械的手,堅定又小心,扶襯著女人肌膚骨肉,深怕弄壞一件透藍琉璃似的。又不當她真正脆弱,她禁得起更粗暴的衝撞,他知道。加快速度,加深力道,汗沿著額頭滴落,滴在她的胸口。
她抬起指尖,緩緩撫摸兩人接合的位置,一片濡濕,再把指頭放入自己的口中。
不斷流出,滴落,更多更多的,愛液,汗水,越來越急促的呼吸。
他壓抑著:「我可以射出來嗎?」
「想射就射。」她說,張開眼睛,望進他眼裡深黑色的欲念,感覺自己是即將迸裂的玫瑰花蕾,「在我面前,你想做什麼,都可以。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