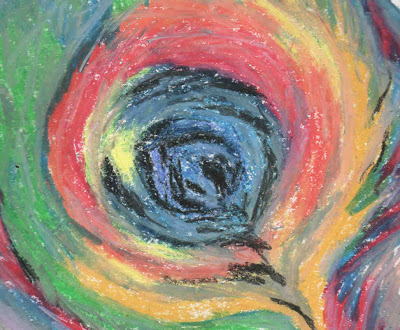文/OrcT
文章同步刊登於OrcT的部落格:歐克踢的小房間。
之三-冒險。
那一天非常神奇,一直到現在都經過那麼久了我都還記得。
那天她進房間的時候,照慣例的在門口逗留一陣子,這陣子我通常只能看到她的小腿跟鞋子,根據我多年觀察的經驗我研判她正在門邊放置鑰匙、皮包這一類的小物品,而且她放置完成之後接下來就會把腳抬起來脫下鞋子,之後會在床邊撩起一點裙子然後脫下絲襪,我承認她搬來的前幾天我有看著這些畫面打手槍,但是現在我已經免疫了!哈哈。
但是今天很不一樣,當她抬起腳抽掉原本的黑色高跟鞋之後,她隨即換上了一雙大紅色漆皮高跟鞋,沒錯,就是那種你輕易的會把「妓女」、「賤貨」、「淫娃」等詞彙連結在一起的大紅色。可能是換上新鞋不習慣或是上了一天班太累了,當她走進房間的時候是異常緩步而且有些搖晃,我這時候以為她是喝醉了,而當她逐漸走進我視線的時候,當我的可視範圍終於可以看到她臉蛋的時候我發現她正在講電話,而且是面露緋紅幸福洋溢的表情,頓時我心都碎了XD。
接著她很緩慢的坐在床邊,不知道為啥她還把話筒拿離臉頰靠近雙腿之間,一陣子之後她再度拿起電話講話,我只能看見側面雖然不能看見表情,但我總覺得她一定是在電愛(職業病?)。
接著,她把穿著大紅色漆皮高跟鞋的雙腿擺上床呈M字型打開,此時我哪管什麼堅持什麼仁義道德,就像你隔壁房間有人在打炮你就會在回過神時發現怎麼手上握有錄音筆而且檔案已經傳上新花魁的s-link了一樣,我見機不可失當然就開始拍啦。
從我的觀景窗望過去的她,百般嬌媚的坐在床上左手拿著話筒右手撫摸著自己,她開始隔著襯衫撫摸自己的胸部,緩慢的用手解開自己衣服上的扣子,她一顆一顆的解,拎杯是一張一張的拍,最後她解開了三顆,開始用手伸進襯衫裡撫摸,此時我很生氣,因為她是側面對我所以我什麼都拍不到。
就這樣摸了三五分鐘之後,她站起身子撩高窄裙面對眼前的衣櫃翹著屁股,左手拿著話筒、右手下探至雙腿之間上下摩擦,我猜想電話那頭的男人一定跟她說著:「妳這剛下班身上還香香的淫娃,我要妳扶著衣櫃門翹著屁股讓我從後面幹妳濕潤的小騷穴!」之類的言語,因為她非常明顯的超級High。就這樣持續撫摸了大約五分鐘之後,她突然身子一抖,身體重心像右偏移了九十度之後往後跌坐,此時她就是面對落地窗(也就是面對我),但因為她有往後跌的關係所以我的可視範圍只從胎的胸前開始。
我看見她的乳房掏出來放在藍色內衣上,胸前乳頭顏色較黑也較大,乳暈不大,整體來說是個不錯的胸部。此時我看不到她的臉蛋,但是由於她是用雙手脫下那雙高跟鞋的所以我研判她應該已經掛掉電話,接著她便自然的脫下膚色絲襪,露出跟內衣一套的藍色絲質內褲,因她股間不料實在不多,所以我想她應該是穿著丁字褲。
接著她從腰間拔出一個東西,那個東西我非常熟,那是小S跳蛋的紅色控制器,因為我都用那一個跳蛋玩弄我之前的那個奴所以真的我非常熟,接著她撥開她的丁字褲,抓著黑色的電線一抽,那個熟悉的紅色小S跳蛋就從她的雙腿之間變了出來,出來的瞬間她還抖了一下XD。
我就說小S跳蛋很強的吧!
在她電愛的過程我打了一槍,並不是因為她自慰很性感,而是因為我在觀察她的情慾。觀察情慾這件事情讓我非常的興奮。
甚至我在電腦裡面整理照片的時候我也興奮到打了一槍,
那種觀察、窺視的快感真的滿足了我某一部分的慾望吧!
—
而在這之後的一週內,我幾乎天天看著她的照片打手槍,有時候精蟲上腦會壞事就是這樣,因為之後她幾乎是恢復了一般的生活,又開始天天過著枯燥乏味的OL生活。
但是我真的好想再看一次這種「秀」,於是我把她電愛被我拍到的一套照片用家裡的canon MG6170印出來,然後在照片後面寫上:「下次穿黑色絲襪配紅色那雙鞋一定會更迷人。」
我印完之後想了一下,還是沒拿出門(弱)因為真的非常變態而且會被抓去關阿=.=+現在想想還真慶幸還好當時理智有回來@@。
後來深思熟慮之後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那就是先跟她混熟一點!
於是我開始每天都在社區中庭活動,因為我有在觀察她所以我都知道她什麼時候會回社區,有時候就製造巧遇讓彼此同時間一起回社區、有時候就先在社區中庭活動等她下班這樣。
一開始只是互相點點頭,後來就開始攀談,她問我的第一句話我都還記得,她問我:「為什麼你的行李都那麼大一包阿?」。
「因為我是攝影師呀!所以裝備真的很多捏~」我刻意這樣子回她,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行業比較特殊很容易就能吸引話題。
「真的唷!!好酷唷,你是拍什麼的?自己創業嗎?拍婚紗嗎?」
聽到這種一連串的問題我就知道她對我充滿著好奇,
接著我就有點興奮,還有點勃起了。
那是一種征服感的投射,我預計她會有什麼反應而她也真的照我腦中劇本走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自己正在一點一滴的吃掉她,正在緩慢的入侵她的身軀、侵蝕她的生活,於是我興奮的勃起。
但我真的不是大變態(認真)
從這次聊天之後我們會開始請對方吃點小東西、像是糖果、軟糖之類的,但是都只是僅限普通朋友的交際這樣,我們彼此也沒留電話什麼的,只知道彼此住幾樓這樣。
終於在有一天的午間,又再一次的巧遇中我把那一套早已印好的妝片裝載純白信封裡交給她,並交待她一定要回房間再看。
我想她也真的有看了,因為從那天之後她就不曾拉開過窗簾了,
一開始見面都一直都是不理我的狀態,雖然我覺得失敗了非常可惜,
可是一方面我也因為她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而感到歡愉。
我想,事情也許就這樣落幕比較好。
可是如果就只是這樣落幕,
那我沒事幹麻花這麼多時間寫這一篇故事來分享勒。
—
之四-合拍。
在她把窗簾關上之後已過半年,我也改掉觀察別人的習慣,這半年來我跟她一直保持著很有距離的禮貌性朋友關係,我們的關係從一開始她裝成沒看見我、到會向我點頭、到現在會偶爾閒聊幾句工作這樣,對她我似乎是有著一種罪惡感吧,所以其實我也都是在逃避她。
直到有一天我們又見了面,她卻從她的包包理拿出當初那個我拿給她的裝有她電愛自慰照片信封給我,然後什麼話都沒說她就跑回家了。
我回家趕緊拿起照片查看,我發現我寫的:「下次穿黑色絲襪配紅色那雙鞋一定會更迷人。」的字下面多了一行:「你真的這樣覺得嘛?0921xxxxxx 打給我。」
那一天,她把窗簾拉開了;而我又把相機架上了。
我不知道她在幹嘛,因為從相機裡面看不到她,
我撥了照片後面的電話號碼,一邊聽著鈴響一邊盯著相機螢幕。
「唯~」這是她的聲音,嚴格來說是一個開關、是一段關係的起點,
「你現在看不見我對不對!?」她的聲音略帶點調皮還有撒嬌的嗲氣。
「嗯。」我已經興奮到必須偶爾揉一下陰莖才可以了。
「我看過你拍的角度,我現在往前走到你只能看到下半身的地方。」
「屁啦,最好妳算的這麼準啦!」我怎麼可能會相信她真的算的那麼準
「你自己看,就是這裡!你現在一定只能看到我的下半身。」
我透過相機看著她家,還真的只能看到她的下半身,她也真的穿上了黑色透膚絲襪以及大紅色高跟鞋。
「妳好性感喔…北…呃…」我本來要叫北鼻,可是後來我發現我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
「喜不喜歡我照你的意思穿呀?偷窺狂先生~」她很機歪的酸了我一下
「我好喜歡妳穿這樣,看起來非常騷,而且非常欠幹。」我沒好氣的回應著她,而她卻開始扭動下軀,刻意地用腳上下擺動輕輕地發出鞋跟碰撞地板的美妙聲音。
「偷窺狂先生可不可以都用這種很兇狠的語氣跟人家說話?人家聽到這種語氣就會變得很濕很熱很騷還很欠幹喔~」
「沒想到你這淫娃口味這麼重呀?還真下賤耶。」
「被你拍到的那天,對方才說要叫十幾個男人輪流插我的淫穴我馬上就爽到倒在地上了…嗯…」
「你在揉妳的奶子嗎?」我從相機理看到她正在亂扭,於是這樣問她。
「對…小淫娃正在揉自己的胸部,胸部好漲乳頭好爽喔…阿…好棒…」
「我要看你這該死的騷貨玩自己…快點弄給我看…幹妳媽的…」
—
她走進我的視野裡頭,面對著落地窗狠力的扯開自己身上穿的襯衫…
「喔~~先生不要~~不要!」
接著她又賣力的把自己的內衣往上掀,讓內衣掛在自己的胸上,她使勁的掐著自己的胸部,手指頭用力的捏著堅硬的乳頭,揉著、拉著、扯著自己早已紅通一片的乳房…
「呀~~~好棒好棒~~用力點,哥哥,用力點玩弄我~」
「我…我…我要舔哥哥的肉棒…」
她靠近落地窗,顧不得可能還有別的觀察家會看見她的淫蕩模樣,她一手拿著話筒、一手揉著乳房,嘴巴貼上落地窗,在我視線裡舔著玻璃…
「就是這…這樣…哥哥妳要讓我…讓我舔妳的肉棒還…還要一邊揉我的奶…」
「喔~~妳這發情的騷貨真的好欠幹阿!」
「對~人家發情…人家欠幹…人..人想要被偷窺狂先生插騷穴…」
—
接著她往後退了一點,一腳跨上床沿撩起裙子之後便用手指把透膚絲襪扯開,接著撥開內褲就把手指往小穴插給我看…
「呀~~哥哥看見了嗎!?好壞好壞…哥哥的手指好壞…」
「好想要好想要…哥哥給…我要肉棒…從後面插…拜託好不..阿~~」
「想到偷窺狂先生在看我的淫蕩我就好興奮」
「到了…到了…到..阿~~」
沒想到她真的爽到一下子便高潮倒地,我幾乎只是個觀眾而已呀!
對於此點我覺得異常可惜,正要說出口的時候他氣喘吁吁的說了。
「156號12樓之7…乎…我現..現在爬過去玄關趴好…門…乎…門沒鎖…
快過來…我…我…呼~我需要你…拜託你一進門就幹我…快點…」
—
她是我旅行的第一個行星,教會了我更深刻的命令以及冷靜的旁觀,
現在我電愛,已經學會要射時偶爾喘個幾下,剩下的時間都在命令、脅迫以及誘使對方說出羞恥的言語了,哇哈哈(得意)
—
行星旅行者,我們下次見XD。